作为军事科学院军史百科部的研究员,钟少异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兵器史、军事技术史、军事史和历代战略的研究,著有相关著作多种,并曾参与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分卷。在他最近出版的《古兵雕虫》一书中,他延续了自己感兴趣的军事技术史、冷兵器以及火器研究。这个访谈,也主要围绕这些方面展开。中国古代的小说、评书等通俗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各类貌似威力无穷的兵器,时常还不乏细致的描写,这些兵器有多少是存在实物,还是说仅仅出于作者的想象?

钟少异:中国古代小说中确实有一些名将的武器,其实是小说家的艺术创造,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在汉末三国时期,并不存在这样的长柄大刀,当时军中大量使用的是长一米左右的环首短柄刀,《三国志》中有许多名将用刀的记载,就都属于这种短柄刀。但罗贯中创造的“青龙偃月刀”也有参照物,这就是宋代《武经总要》中著录的“掩月刀”。对这种现象,还需结合中国文学史来看。中国古代小说是随着宋以后市井文化的发达而走向兴盛的,大量作品产生于明清时期,其中反映唐以前的战争史事,写到兵器,作者便多有创造或改造,而且基本是参照与作者相近时代的熟悉之物,与历史原貌大多不符;如果写的是宋以后的事情,则接近于当时人演绎当时事,有关兵器的描写也比较近真,甚至可以当史料来用,比如《水浒传》。
在这些作品当中,武艺高强的人常被描述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钟少异:“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大致是在宋元时期出现的。南宋宁宗朝的武状元华岳(人称翠微先生)所著《翠微先生北征录》中说:“臣闻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这是较早的记载。此后“十八般武艺”一语在元明杂剧、话本和小说中广为流行,并由“十八般武艺”衍化出了“十八般兵器”的说法,如关汉卿《哭存孝》中说:“你放下那一十八般兵器,你抡不动那鞭、简、挝、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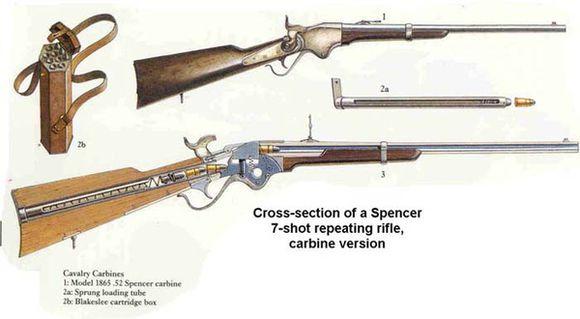
关于“十八般武艺”的具体内容,有多种说法。《水浒传》第二回说是“矛锤弓弩铳,鞭简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杈(杈或作朳)”。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五中说是“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杷、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关于“十八般兵器”的具体内容,说法更多,有人统计总在十种以上,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简锤抓、鎲棍槊棒、拐子流星,其内涵实质也是关于这些武器的习练技艺。在中国传统武艺中,弓射之术本有极重要的地位,宋人甚至说“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称首”,但后来由于火器特别是铳炮的发展,弓的地位逐渐下降,及至晚清,习练弓箭者越来越少。由“十八般武艺”衍生而来的“十八般兵器”的具体内容中往往没有弓箭,就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向。
中国古代的兵器及其习练技艺远远不只十八种,“十八般武艺”和“十八般兵器”其实都是概举,举其要者。之所以举了“十八”之数,与中国古人尚九及九的倍数的习俗有关。“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九者,阳数之极也。所以古人举数物事,常喜欢凑成九、十八、三十六等,如九天、九州、十八拍、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一百零八将,等等。印度传来的佛教,本只有十六个罗汉,宋时有人在十六罗汉外又加了两名,凑成十八罗汉。久而久之,民间盛称十八罗汉,反不知正宗原是十六罗汉了。钟少异:在冷兵器时代,列阵战斗是基本的作战方式。中国古人所谓“阵”,其实就是军队战斗队形。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战斗队形大多呈密集厚实的方形或长方形,所以今人就把那个时代的作战方式概称为“方阵作战”。“方阵”一词,狭义指方形战斗队形;广义泛指密集厚实的整齐战斗队形,多数是方形,也有非方形者。“方阵作战”概念就是用其广义。

方阵作战的基本要求是厚集兵力,统一步调,形成强大的集团冲击力或坚强的整体防御。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基本是方阵对决,以整胜乱、以整胜散是基本规律——哪一方的阵形先乱,哪一方的阵形先散,哪一方就必然归于失败。因为保持整齐队形的集团方阵,其强大冲击力或坚强防御力是任何散兵游勇所难以对抗的。所以古代实战阵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厚集兵力,整齐统一,即以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密集厚实的整齐集团队形,步调一致、行动统一,其方法并不复杂,其特点就是厚集兵力,简单实用,统一整齐。越复杂的阵法,必然越难以统一一致,往往不足以胜敌,反而自乱阵脚,自取其败。
阵法发展到后来,被渲染得神乎其神,出现了“八卦阵”、“天门阵”这些东西?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已经神秘化了的阵法?
钟少异:中国古代阵法理论发展之所以与简单、实用的实战阵法相背离,走上神秘化、复杂化的玄虚道路,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兵阴阳理论的盛行。战国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学说趋于成熟,逐渐成为中国人看待宇宙万物世界万象的基本方法论。受此影响,在军事领域也产生了兵阴阳学派,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预测、分析、阐发战争和军事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兵阴阳理论。汉代将兵家总分为四派: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汉书·艺文志·兵家》述兵阴阳理论:“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斗击,北斗所指,泛指星象;五胜,五行相胜。)这一派人多为占星望气的方术之士,排兵布阵之法是其热衷探讨的重要问题,他们没有实战经验,却有基于阴阳五行理论的成套推演方法,其阵法理论,遂越来越脱离实际,而趋向神秘化。
二是文人论兵风气的盛行。文人论兵,发端于战国时期,渐成风气,其流弊便是“披甲者少而言兵者众”,“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益弱”(《韩非子·五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纸上谈兵,不切实用,夸夸其谈成为时尚,反而败坏了社会风气。中国历史上文人论兵的风气在宋、明两代达于极盛。众多文人学士,热衷于谈兵论战,他们没有实战经验,又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强烈影响,更进一步加重了军事理论特别是阵法研究的神秘化和复杂化,于是,在阵法研究中形成了文人论兵和兵阴阳理论的合流之势,大量的兵书,纯粹从兵阴阳的理论模式——诸如阴阳五行、太极两仪、八卦九宫,等等,推演出了五花八门的复杂阵法,玄而又玄,在实战中则完全难以运用,其末流甚至堕落为奇门遁甲的法术。宋、明两朝,兵书撰著之丰创造了“世界之最”,而在实际战场上则疲弱不振,屡战屡败,与此不无关系。了解了中国古代实战阵法与阵法理论之间存在的悖反现象,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阵法研究采取正确的态度,这就是必须以实战为依归,力求把握其实战性特点,切忌堕入传统阵法理论神秘化、复杂化的误区。
说到阵法,让人联想到战车。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中似乎经常用到战车,但到了两汉时期似乎就慢慢地淡出了。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呢?钟少异:你所说的战车应是特指古典战车,即独辕的马车,用于搭载将士冲锋陷阵。在世界古典时代,这种战车在东西方都有广泛使用,在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和中国夏商周文明中都能够看到其踪迹,尤其中国对古典战车的运用是相当突出的。经过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发展,古典战车的运用在春秋时期达于极盛,常见一战萃集上百辆以至数百辆战车。众多的战车搭载兵士,列阵交战,气势磅礴,“如霆如雷”,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这与西方古典时代一般只在战争中使用少量战车,主要由将帅及其亲随武士乘用有很大不同。由此在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车战时代”的概念,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主要使用战车作战的时代。

不过,现在我们对“中国车战时代”的研究还没有完全突破一个难题:大数量的战车如何列阵、如何交战。古代武士搭乘马拉战车,必须接触战斗——虽然可以在一定距离用弓箭对射,但最终双方必须接触厮杀。历代注经学者对春秋车战的列阵方式做了大量考证,今人也根据考古发现的商周战车遗迹进行了复原探讨,但迄今的研究复原基本只适用于少量战车列阵或单排列阵的方式。然而在实际中,大量战车参战,不可能只是单排列阵,试想几百辆战车一字排开,得有多宽广的战场,兵力这样分散又怎能有效攻防?那么,如果多排纵深列阵,敌对双方的车阵又如何交会交战?对两千多年前的将帅来说,这是个很棘手的实战问题,弄不好可能只有第一排的战车能与敌人交上手,后面的战车则自我拥挤、互相碰撞、乱成一团,不用打就垮了;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个很不好解决的学术难题,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复原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春秋多排制车阵模型,进而令人信服地建立起春秋时代大规模车战的历史图景。
但不管怎么说,春秋时期集中使用大量独辕马车搭载兵士作战的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古典战车运用的衰落,开始于春秋晚期,主要原因是争霸战争发展导致作战地域扩大,战场环境日益复杂化,只适于平原旷野驰骋的马拉战争越来越难以适应,于是步战复兴,步兵得到大发展。战国时期骑兵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战车的衰落。战国晚期秦、楚等大国的军力结构都是“车千乘,骑万匹,带甲(或持戟)百万”,军队的主体是带甲持戟的百万步兵,战车和骑兵都起辅助作用,其共同特点是机动性好、突击力强,但骑兵的适应性更好,所以当汉武帝大力发展了骑兵之后,古典战车就完全退出了战争舞台。与此同时,汉代兴起了双辕的畜力车,主要用于运输,在军中也有广泛使用,除了载运辎重,也用于防御设障,后人有时也称之为战车,但与古典战车已完全不同。
从战国、秦汉起,就出现了强弩这种兵器。历代记载不少。《战国策·韩策》记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汉代许慎说天下好弩材料中有“溪子”。居延汉简有“大黄力十石弩”的记载,三国两晋以及隋唐一直都有著名的弩出现,如众所周知的诸葛连弩。晋代还有一种腰引弩,《马隆传》里有记载。到了宋朝,西夏又有神臂弩,在您看来,这些弩的真实性有多高,它们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大的威力吗?钟少异:你提到的关于弩的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而非虚幻的传说。需要区分的是,其中有些是手持弩,有些是安装在架上发射的弩砲。能射六百步外的,应是弩砲,其弩力极强,需用绞车张弦,所以古人称之为“车弩”“绞车弩”。秦始皇在海边射巨鱼,就是用的这种弩砲。汉简有关弩力的记载,甚至高达“四十石”。我曾作过粗略分析,汉简所记十石以上的弩,有些是弩砲;二十石以上的弩,应都是弩砲(见拙著《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上古至五代卷,403-406页)。
中国手持弩的发展高峰是在汉代,李约瑟曾对汉代的青铜弩机赞叹不已,认为是古代机械工程技术的杰出成就,可以与现代的“来福枪机”相媲美;弩砲的发展高峰是在宋代,宋人将弩砲称为“床弩”或“床子弩”(床或床子即指安装弩的架子),宋代床弩的射程达到“千步”,约合一千五百五十米,这大概是冷兵器时代抛射武器射程的世界之最。床弩在元代仍有使用,蒙古军西征也用了床弩。宋元时期还用床弩发射用火药制作的燃烧弹和爆炸弹。到了明代,床弩就从战场上消失不见了,其原因主要是火器发展起来了。但手持弩的情况有些复杂。在汉代之后,中国的手持弩技术就陷入了停滞,非但没有进步,反而逐渐退化,到了宋元明清时期,虽然军中一直也使用一些手持弩,但精妙的汉代青铜弩机却失传了,宋元明清时期的手持弩,大体就类似于我们今天在西南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还能够见到的那些狩猎用弩。中国弩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中的历史原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还需要深入调查研究。

说到发展停滞,有一个问题很受关注:中国为何在火枪出现后的几百年里,没有大规模出现西方那种“排队枪毙”式的火枪阵,而是一直将弓在军队里使用到十九世纪?有的冷兵器研究者比较了中国的反曲弓与火器,得出结论说,中国因反曲弓比火绳枪乃至燧发枪都强,所以长期压制火器发展,对此您怎么看?钟少异:这种现象确实说明中国早期火器发展缓慢,难以淘汰冷兵器,所以形成了与冷兵器长期并用的局面。其中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还是古代中国的文明特性导致火器发展的动力不足。中国早期火器的发展曾经历了两次严重的停顿。自从我们的祖先在北宋初把火药应用于军事,创制出世界上最早的火药兵器后,在南宋和元代,中国早期火器有了突出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爆炸性火器从纸壳发展到铁壳,出现了铁壳爆炸弹;管型火器,从纸管、竹管发展到金属管,从喷射火焰发展到发射子弹,出现了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这是后世枪炮的鼻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出现了反推式的火箭。
到了明朝永乐时期,开始于北宋的中国早期火器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时,金属管型射击火器——铜火铳代表了火器技术的最高水平。永乐时期的铜火铳,两种类型,手持铳和架射火铳,结构上、制造上,比起之前洪武时期和元朝的铜火铳都有很大的进步,而且非常规范。从现在发现的元明火铳来看,管型火器进入金属管时代以后,逐渐表现出了规范化的迹象或趋势,在永乐时期,规范化程度就比较高了,比起之前的洪武火铳和元火铳都明显突出。达到这个高峰以后,中国早期火器的发展也就停顿了下来。永乐之后,从宣德到正德的一百来年,中国火器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发展表现,基本就处在停滞的状态。而且,与永乐火铳相比,从宣德到正德时期的铜火铳反而有退步的迹象,一是制造没有永乐时期精细,二是规范性降低了。所以这一百来年,总体上是停滞和退化。
从嘉靖时期开始,中国火器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趋势。这是因为西方火器传来所刺激、所带动的。首先是西方的佛郎机炮和火绳枪(鸟铳)传来,中国进行仿制,这是从嘉靖时期开始的,这标志着中国火器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接着,在天启、崇祯时期,西方的加农炮——西洋大炮(又称“红夷炮”、“红衣炮”)传来,中国又进行仿制,火器技术又上了一个台阶。然而,以仿制西方火器为主的中国火器的这个发展阶段,从明朝嘉靖时期开始,经过万历、天启、崇祯时期,持续到清朝康熙前半叶,也就终止了。这一停止是非常明显的,基本上是清朝统治者自动放弃发展。
明末清初仿制西洋大炮,主要是依靠传教士来设计、指导和监造的,康熙年间南怀仁贡献最大。康熙初年,内乱外患迭至,应军事急需,南怀仁帮助清廷铸造了大量火炮,在平定三番、平定准噶尔、统一台湾、抵御沙俄入侵黑龙江等一系列战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明末以来对西方火器的仿制达到了高潮。康熙二十八年,海内基本安定,清廷根据南怀仁的设计,铸成了六十一门重型火炮——“武成永固大将军”,代表了明末清初中国仿制西方火器的最高水平,也标志着明末清初仿制西方火器高潮的终结。这之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朝就再没有造过这样大型的火炮,清廷也渐渐不再重用传教士,火器方面的发展基本停止,又陷入停滞和退化状态。如果说乾隆时期火器技术还勉强保持了康熙时的水准,那么乾隆之后,就越来越不济了。直到鸦片战争时,清朝的火器制造仍然还是遵循康熙时的“祖制”,但技术全面退化。鸦片战争爆发前,东南沿海地区为加强海防,按照祖宗的老法式赶造了一些大炮,其技术水平和质量,明显还不如乾隆、康熙时期。

中国早期火器发展的这种自我停顿现象,用反曲弓的压制来解释,恐怕简单化了,也说不太通。明末清初引进的西洋大炮,其威力早已远超反曲弓;当时欧洲燧发枪也已传入中国,但清人根本不加以发展推广,而欧洲正是通过不断改良推广火炮和燧发枪,在十七世纪末彻底淘汰了弓箭手长矛手。为什么中国不进一步发展推广西洋大炮和燧发枪?在康熙、乾隆的心目中,显然是有点西洋大炮和鸟铳(火绳枪)就足矣。对此,我深感有必要从古代中国的文明特性来分析探讨深层次的根源,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学术课题。
古代制造兵器离不开钢铁冶炼技术。现在有些军事爱好者对中国古代的铸铁技术推崇备至,对西方古代主要的冶炼产物熟铁非常不屑。对这种技术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知您怎么看?钟少异:中国古代钢铁冶炼技术的突出特点是形成了以生铁冶炼为主的技术路线,这与欧洲长期沿用块炼法冶锻熟铁的技术路线相比,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冶炼液态生铁显著扩大了炼铁规模,能够获得大量铁原料;二是用液态生铁进行铸造适于大批量生产铁器。但生铁质脆,生铁冶铸不适于制造兵器,所以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生铁治铸已有规模化发展,但主要是生产农具,这个时期的铁兵器仍然主要用块炼法冶锻熟铁的方法制造。之后,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将生铁炒炼脱碳以获得熟铁或钢的技术(对这项技术,以往都沿用现代术语称之为“炒钢”,华觉明先生认为,中国古人炒炼生铁基本上是对含碳量不加控制地一炒到底,获得的大多是含碳很低的熟铁,更宜称之为“炒铁技术”),才从根本上克服了生铁不宜制造武器的难关。这项技术在西汉时期迅速推广,才使铁兵器淘汰了青铜兵器,由此也确立了中国古代铁兵器的基本制造方法:即炒炼生铁获得熟铁,用熟铁增碳折叠锻打制成兵器。这个方法,可以说继承、融合、升华了早期冶锻块炼法熟铁的技术;不仅用于制造兵器,也广泛用于制造优质的农具和手工生产工具。因此,我认为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特点不能仅仅概括为生铁铸造或生铁冶铸,而应概括为,以生铁冶炼为基础,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冶炼液态生铁,用生铁进行铸造;炒炼生铁成熟铁,用熟铁进行锻造。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这两个方面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我们研究探讨问题时不可偏废。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在马镫出现之后,骑兵才能成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那么,除了自幼生长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的骑兵是不是直到马镫出现后才能获得决定性的地位呢?杨泓先生说,“人们对于完备马具的需求情况是:过着游牧生活的骑马民族并不迫切,而非骑马民族为了掌握骑术,自然更迫切地求助于完备的马具。”也就是说,他认为,农耕民族的需求更为迫切,科技水平更高,于是率先研发出了马镫。对此您怎么看?
钟少异:关于马镫发明的意义,我觉得需从三点来看:第一,评价马镫的意义,首先要看到在马镫出现之前,骑兵已经有较长的历史,并且已经在世界战争舞台上创造了壮观的业绩。发生在东亚的汉匈战争,其决定性的作战方式就是在广阔草原上进行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对抗,这些骑兵都是无镫骑兵。第二,要看到发明马镫的四世纪,正当欧亚大陆上开始形成骑兵重装化的发展浪潮,其表现是骑兵和战马都披上铠甲,骑兵铠甲更趋完备,由防护严密但机动性较差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即后世所谓“拐子马”)组成严整的阵形互相碰撞厮杀。对重装骑兵来说,马镫是上马时登踏借力和骑乘时稳控战马的急需之物,如果没有马镫的借助,穿着笨重的骑兵要爬上同样穿着笨重的战马会非常困难,而要想在马背上骑稳当就会更加困难。因此,马镫的发明与中古时代的骑兵重装化趋势密切相关,其最直接的重大作用就是解决了重装骑兵的骑乘问题,由此促成了欧亚大陆骑兵重装化浪潮的到来。第三,有了马镫,骑马更加安稳,训练骑兵更加容易,骑兵也能更好地发挥战斗效能,因此马镫的出现标志着骑乘马具的完善,也标志着骑兵装备的完善。七世纪后重装骑兵在欧亚大陆上逐渐退潮,骑兵的主体恢复了轻捷快速的传统——人着甲马不披甲,但鞍镫齐备,组训和作战更加便利有效。这时,习惯了鞍镫齐备的骑乘者,要他们再像老祖先那样去骑无镫马,势必困难重重了。
杨泓先生是国内最早关注马镫发明问题的学者,他的观点很有道理。目前在中国东部的农耕地区发现了马镫发明的完整证据链,即从单镫到双镫的较丰富的实物和图像资料。这些资料说明,古人先是在马的一侧装一个小镫,仅供上马登踏,骑好后就不再使用;之后才发展为在马的两侧都安装上镫,供骑乘时双脚踩踏。从出现单镫到形成双镫,在不长的时段内就完成了,根据中国的资料,这个发明过程发生于公元300年前后,至迟四世纪初已有双镫(参见拙著《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上古至五代卷,497-500页)。其时中国正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骑兵重装化的浪潮迅速兴起,铠马骑士成为战场上的主力,也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标志(时人将着甲的战马称为“铠马”,据《晋书》记载,石勒大败姬澹时俘获铠马万匹,姚兴击败乞伏乾归,收铠马六万匹)。

您自己写过一篇《6-8世纪中国武器中的外来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关键性的外来影响呢?举个例子来说,元代的襄樊之战,元军使用了“回回砲”来攻打樊城、襄阳城,而这种兵器是由回族学者发明的。套用时髦的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中国兵器发展的“内亚性”?钟少异:古代兵器的传播交流及其影响,是技术史、军事史也是文明史研究应关注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各方面对这个内容都还注意不够,研究非常有限。除了少数问题,如对火药西传和早期火器东西互渐的研究较充分外,大量问题都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我自己对这个方面也缺乏研究,知之甚少。当初写《6-8世纪中国武器中的外来影响》一文,主要是因为读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觉得书中有关唐朝武器中外来物的论述过于薄弱且不够准确,于是略述个人所见,实在也是很没有系统性。
你提到“内亚性”的问题,确实,在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关注亚洲内陆文明及其与中原文明的互动关系,需要关注亚洲内陆文明在沟通东西方中的作用。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和军事技术的传播交流问题,也很需要有这样的视野。火药西传是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在宋元时代,中国人发明的火药通过丝路贸易和蒙古军西征传到阿拉伯地区,进而又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对欧洲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的这种结果,离不开诸多亚洲内陆民族的活动。又比如抛石机的传播。在火炮发明之前,抛石机是威力最大的攻城武器。古代抛石机有人力曳索式和配重式两种主要类型,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曳索式抛石机,传到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人对其进行了改良,发明了威力更大的配重式抛石机,蒙古军南下攻宋时,从阿拉伯地区引进配重式抛石机,终于攻陷久围不克的襄阳城,打开了灭亡南宋的大门,中国文献中因而把配重式抛石机称为“襄阳砲”“回回砲”。但目前对抛石机的研究和史料挖掘还不够充分,其传播改良过程中的许多情况不甚了了。
类似还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以内陆亚洲乃至欧亚大陆的广阔视野去把握,而国内学术界目前的工作都还比较初步,比如冶铜术的起源和传播,冶铁术的起源和传播,马车的起源和传播,骑马的起源和传播,骑兵重装化浪潮的兴起、传播和衰落,等等。深入地究明这些问题,才能对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互动和发展建立起真切的图景,这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历史故事
历史故事




























